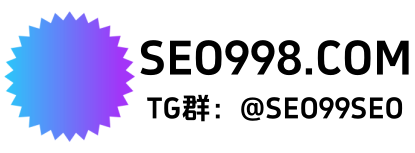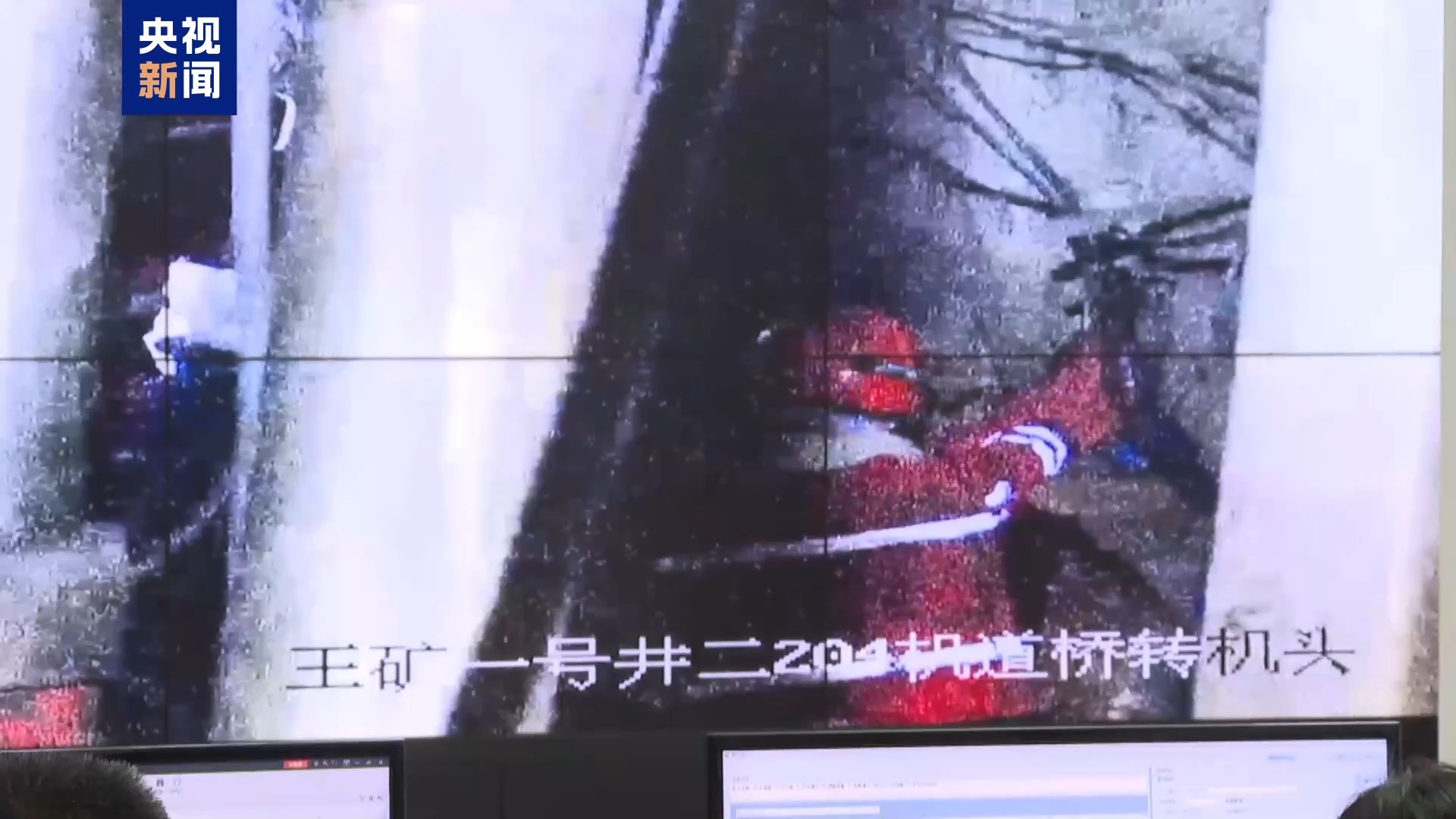中国青年网娱乐:17cgcg吃瓜网黑料爆料-黑料老司机吃瓜不打烊-痴情与真爱
【编者按】520因谐音“我爱你”而成为中国现代爱情表白日的数字密码。在四百年前的中国,爱情也曾有过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一书中,英国学者潘翎通过冯梦龙的《情史》,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的复杂内涵。冯梦龙笔下的“情”,远超男女之爱,是一种对他人痛苦的共情能力,一种道德与美学兼具的敏感性。冯梦龙文集中荒诞离奇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中西方对爱情本质理解的深刻差异。本文摘自《真爱遗事: 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英] 潘翎著,宋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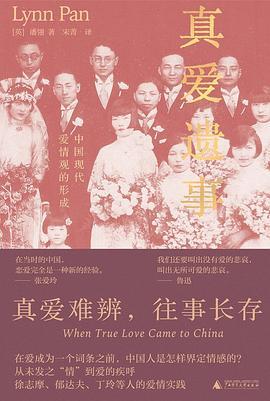
在受到20世纪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前,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人对权威、礼仪以及情爱关系——本书的重要话题——态度的默认设定。在情爱关系方面,家庭就是一切,不孝儿女是不可想象的。婚姻的主要目的是延续家族血脉,妻子对丈夫的忠诚——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丈夫家族的忠诚——必须是彻底的。事实上,人们对妻子贞洁的期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她如果早年丧偶或受到奸淫的威胁,会以自杀来维护自己的清白。这些所谓的“性英雄主义”行为赢得了公众的钦佩,还有政府的嘉奖和表彰(见第12章)。
如果她们真的自杀了,不是因为忠义的儒家美德,而是出于“情”,人们会赞颂她们吗?宋明理学影响下对情感抱以怀疑态度的卫道士肯定会说“不”,但对于集作家、出版人和文学家于一身的冯梦龙(1574-1646)来说,这种区别是模糊的。在他看来,“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此外,无论是忠是孝,贞洁还是英雄主义,作为一个原则来执行是强制性的,而出于热情去做是真诚的。
冯梦龙生活在17世纪的明末,因其对“情”的接纳而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史上脱颖而出,在今天许多英文写作的中国研究者看来,这种接纳所达到的高姿态足以称得上是一种崇拜。将其描述为“浪漫的情感主义”的兴起未免有些牵强,但有一种观点透过当时的作品表现出来,即各种形式的人类情感都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体验而被关注,并得到直接的表达,这种信念也的确得到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的赞同声。
冯梦龙通过一系列的故事、传奇和逸闻表达了自己对“情”的观点。在序言中,冯氏宣称自己是一个情痴——他的情意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他遇到另一个情痴时,就会想要拜倒在他面前。如果不能帮助别人减轻痛苦,无论这个人是否为他所识,都会使他感到忧虑,甚至叹息好几天,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为了激发人之情,他不惜创立一种“情教”来教导人们。一旦个中要义普及开来,子对父、臣对君都将体会到这种感觉,其最终将如春花绽放,欢乐和喜悦被传递给所有的生物。冯梦龙把“情”比作一根绳索,把分散的钱币串在一起,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全世界为情所系,成为一个大家庭。“只有维系!”这或许可以成为他的座右铭——E. M. 福斯特(E. M. Forster)所说的“无苦无怨地维系一处”,直到“天下者皆兄弟也”。
冯梦龙文集以“情史”为名,这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名称,其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历史事实的依据。在英文中,这个标题常被译为“爱的解剖”。把“情”翻译成“爱”就已经足够了——“爱”这个词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含义。然而,令我困扰的是,“爱”并非冯梦龙所说的,是当看到痛苦却无能为力时的夜不能寐。他所感受到的肯定更像是同情或一种进入他人的共情能力,所以当他继续说“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时,他的意思一定是伤害他人就是伤害自己人的感情。在序言的另一处,他建议,不妨摆脱佛的慈悲和孔子的仁义,因为“情”可以取而代之。
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很难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冯梦龙所说的“情”是一种对他人感受的“敏感性”(sensibility)。事实上,当我阅读冯梦龙的序言时,“情”(敏感性)这个词一直吸引着我。我联想到的并非这个词的现代含义,而是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被赋予的意义。这个词在1750年后流行于英国,文学家们谈论“感性崇拜”或“情感文化”来描述感伤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当时这个词的含义比现在要强烈得多,指的是对他人的一种超乎寻常的反应能力,或者是一种同时包含了道德与审美的敏锐感受,以及对美好事物和他人的痛苦的感知能力。如今,道德的内涵常常被遗忘,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除了由我们现在称之为同理心的情感所激发的善举外,因同情而流泪的倾向也标识出富有教养的敏感性和道德价值。
敏感性是从理性和判断(也就是简·奥斯汀小说《理智与情感》中的“理智”)向情感整体转变的基本原理中的一个关键词。虽然中国人对“情”的崇拜并不完全是重感情而轻思考、重激情而轻理性、重怜悯与仁爱的本能而轻社会责任,但其仍将感情置于首位,认为感情比虚伪的惯例更能指导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声称表达感情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与孝道、忠诚、无私的仁爱和贞洁这样的儒家最高价值观并行不悖。
早些时候,我以“man of Feeling”来对应冯梦龙“情痴”的自我形容,正是借用了亨利·麦肯齐(Henry Mackenzie)的《感性的人 》( The Man of Feeling, 1771)这个书名。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学人物,比如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笔下多愁善感的旅行者,歌德创造的维特等,都体现了敏感性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指责冯梦龙缺乏敏感性,他声称自己时常处于癫狂状态,敏感性已濒临极端,但要补充一点,这不等同于那些被英国评论家们描述为感伤主义的夸张形态——神魂颠倒、泪水湿透的手帕、感情流溢、自我陶醉——即一种在18世纪被肯定为“敏感性”但在当下不受推崇的概念。
《情史》的序言就谈到这儿,后面的故事就是个大杂烩,其中反复出现中国文化想象中的熟悉元素——侠义、缘分、酬金、梦、复活、鬼魂来访、超自然现象等。我将从文集的数百个故事中随机挑选三则在此复述。
王某,以倒卖木材为业,与妓者唐玉簪相好,后者擅长歌舞杂剧。鼓楼东住着一位爱好音乐的周郡王,传唤她到自己的宅邸来。玉簪深受郡王喜爱,后者因此花重金从鸨母处为她赎身。王某思念成疾,贿赂王府中的老女仆传话给玉簪:“倘得一面,便死无恨。”玉簪找机会对郡王说了此事,郡王开玩笑说:“须净了身进来。”王某听闻立刻自宫,差点死去。三个月康复后,王某去了郡王府,郡王让人解下他的衣服查看,然后笑着说:“世间有此风汉。既净身,就服事我。”王某谢过郡王,后者带玉簪前来与之相见,二人泣不成声。郡王赏给王某千两黄金,每年靠收利息为生。
冯梦龙对故事评论道:“是乃所以为情也。”爱一个人,就代表着想和他或她一起享受性的欢愉。阉割让这种快乐消失了,却没有让爱消失——王某正是如此。所以,冯梦龙得出这样的结论:“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在这一点上,冯梦龙似乎在对欲望和爱情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比我读过的任何与之同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更加明确,但实际上,他只是局限于指出王某对玉簪的感情痴至超出了任何性满足的可能性,这让它更像一个“情”而非“淫”的例子。冯梦龙继续道,如果王某是那种为了新欢而抛弃旧爱的人,那么驱使他的将是一种尚未满足的欲望,这其中爱在哪里?因为王某已经去性别化,他的感情不可能只是彻头彻尾的欲望——他对玉簪情感的延续证明了这一点。有些人准备为爱情献出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为之自宫了。尽管如此,冯梦龙总结说,可以承认王某的爱,但说他不痴傻就讲不过去了。
第二个故事不过是一则趣闻,讲的是两个商人,他们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天,年轻的那个肚子痛得受不了,年长的那个就竭尽全力照顾他,医治他。幸运的是,病人痊愈了,大约十天后,变成了一个女孩。这事太怪诞了,当局特意向朝廷报告了此事,由于两人都尚未婚配,朝廷允许他们结为夫妻。冯梦龙对此唯一的评论是:既然这两个男人是好朋友,他们也可以不变性就结婚。
这则轶事出现在专门讨论变身主题的章节中,这一章还包括了女人变成石头,忠诚的夫妇在死后变成一对仙鹤,恋人变成双飞的蝴蝶等故事。读这本书时,我想起了奥维德在《变形记》中重述过的所有关于希腊和罗马魔法变身的传说。我特别想起了伊菲斯(Iphis)的故事。伊菲斯是个女孩,从小被当作男孩养大,当一直隐瞒她性别的父亲安排她与另一个女孩结婚时,她变成了男孩。但在奥维德的书中,这种转变是由女神伊希斯(Isis)完成的。而在中国的故事中,没有任何外部因素参与其中,似乎只要有情感纽带就足够了。
第三则故事讲述了吴淞的孙生,年方17岁,姿容俊美。孙生与邻家女孩互生情愫,但无法亲近。一天晚上,女孩的母亲要如厕,孙生误以为是女孩,向她扑去,当看清面目时,慌张而逃。母亲怀疑女儿在背地里鬼混,于是对着女儿一顿责骂。女孩羞愧难当,一气之下悬梁自尽。母亲见女儿气绝,设法加害孙生来为女报仇,“某与若门第相等。苟爱吾女,即缣丝可缔,何作此越礼事?”她强迫孙生与她回家,将他绑在女孩的尸体上,并向衙门报案。
毫无疑问,孙生将被处以死刑。他心想,我跟这个女孩连一晚上的欢愉都没有过,现在却要被处以极刑——这一定是恶有恶报,让我走到了这一步。正当郁郁寡欢之时,孙生注意到女孩颜面如生。于是,他忍不住亲热一番,这样他就死而无憾了。令人惊讶的是,欢爱之后,女孩复活了,恢复了呼吸。不久,母亲领着差人到家,进门却看到两个年轻人正并肩而坐说着话。她对此一头雾水,但仍将孙生绑至衙门。孙生说明了一切,知县判定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遂做主让二人结为夫妻。
冯梦龙希望用这几个故事来说明“情”的神奇力量,它的效果甚至超越了死亡,这里的“情”显然是性欲。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与尸体发生性关系很恶心,恋尸癖现在被认为是一种触犯法律的性变态,但中国故事以模糊活人和死人的世界为乐,而孙生的行为也无异于那些讲述男人与女鬼或狐狸精交欢场景的流行而又挑逗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喜剧效果,而非病态行径。
此外,肉体欲望的圆满难道不是赋予生命,繁育后代吗?如果可以生育,为何不能重生?无论如何,孙生和女孩的结合是命中注定的,即使不在天宫,在冥府里也是注定的。对县太爷来说,缘分的昭示已经足够圆满,他没有干涉这对恋人的婚姻命运,而是成人之美。孙生想象中的恶业最终被证明是良性的。正如无数中国故事一样,意外姻缘背后的业缘是冯梦龙书中一个明显的主题,而且至今仍然是普通中国百姓的表达方式甚至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第二和第三个故事都出自“情灵类”这一章,以情感与神迹的结合为主题,第一个故事则出自“情痴类”这一章。冯梦龙的每一章标题都以一个广泛的类属来同“情”进行配对,从相亲、贞洁到妖魔鬼怪。有几个类别可以用来限定“情”,如将“外”与“情”搭配在一起,暗指“同性之爱”。这些搭配表明,对于冯梦龙和其他同道中人来说,“情”与一整套观念、个人特质、价值观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其中,痴情和侠义是两种特别值得仔细研究的类别。
我所说的“痴情”是由两个词组成的:情和痴,后者在字典中的标准定义为“白痴”或“疯狂”。在讲述王某和唐玉簪的故事时,我将其译为“daft”,因为这个英文单词不仅意味着“愚蠢的”“疯狂的”,还意味着“痴情于”,而这的确是王某的形象。他对唐玉簪痴迷到了极端的程度,为了看她一眼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命根子。这看起来很愚蠢,但作者认为这就是痴情的表现。
本章题词“自达者观之,凡情皆痴也”出自冯梦龙之口,他把爱变成了痴情的同义词。对于中国人来说,“痴情”是指愚蠢而过度地迷恋某人,但这个中文措辞并不同英文一样意指“痴情”是一种短暂的状态而非“真实的东西”。对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15世纪一位画家创作了木刻版画,画中是一位年轻女子和她的女仆从屏风后注视着一对正在交配的猫。标题的四行诗唤起了一种梦幻般的倦怠情绪。梧桐叶落,少妇发呆,不知已是秋天。我们可以很容易从正在交配的猫身上读到:她很“痴情”,而她的迷恋带有性渴望的意味。
第二个例子,把时间往后推三个半世纪,到了小说家吴趼人(1866—1910)的时代。吴氏惊呼:“情,情……岂是容易写得出,写得完的么?”将“情”局限于两性之间的欢愉是对它的狭隘和玷污。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的表现形式取决于它指向谁。如果指向领主和国家,情就是忠诚;对父母,就是孝顺;对孩子,就是亲切;对朋友,就是坚定和团结。至于男女之间,那只是一种痴情,而当情没有得到回报,却还要为对方挥霍无度时,它就无异于“蛊惑”了。
有人猜测,吴趼人说的是一个被迷惑住的人,特别是在感情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被下了魔咒。他贬低这种情感,并不止一次地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习惯称之为“情”,这是对“情”的轻视或诋毁。在他看来,痴情已是浪漫爱的全部。
为什么我对痴情如此重视,人们却对它不屑一顾,因为它使我能够在中国和西方的浪漫爱概念之间进行对比。对于吴趼人和冯梦龙来说,所有的爱情都是痴情,与其说痴情廉价,不如说爱情廉价。他们习惯于将浪漫爱视为禁忌之爱,而不会有其他想法,因为它在婚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坠入爱河必然与父母权威和传统道德相抵触,因此是不合法的。
相比之下,“痴情”在英语世界里并不等同于“真爱”。约翰·阿姆斯特朗试图在《爱的22种底色》中有关痴情的一章里对其进行定义。他问道:“我们能否通过‘痴情’中缺失的东西来洞察真正的爱?”他指出,我们“想说的是,‘痴情’和真正的‘爱’之间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他所谓的“爱的影子”和“真正的爱情”之间是有区别的。然而,他无法令人信服,他的举例并不能被视为“坠入爱河”的缩影。
切开爱情之瓜的一种方式是将“坠入爱河”或在“恋爱中”的状态标记出来。海伦·费舍尔的研究表明,从不同的大脑回路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对神经科学家来说,“恋爱中”的状态是痴情、深恋、热烈的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浪漫爱。当人们不想承认“痴情”和“爱”之间有区别时——在中国的传统中肯定没有区别,你会像吴趼人和冯梦龙那样得出结论,浪漫爱是“痴情”的同义词。